
文|姜姜湖
图|杜娟娟
城里的人若是乡下无亲便多少有些悲哀,口福就如那旱季的湘江河,浅了许多。
家里人都在长沙,像我这种一不官二不富的家庭,平日也无礼可收,所以极少能够与那乡野田间充满烟火气的好食材结缘。
儿时对腊肉无感,是因为根本就没吃过什么正经玩意。
湖南许多地方把熏腊肉叫炕腊肉,就凭当时城里筒子楼里都是一水的燃气灶,哪里有什么条件去“炕”哟。菜市场里农村大妈售卖的货色,又怎么可能是自家灶台上挂的硬货?真正的好东西自家吃怕都不够。
院里的阿姨们在冷天,偶尔会在楼下支个铁皮桶子,挂几块肉点燃锯木屑熏个一两天,待那肉变色,香味刚刚飘出来,就草草收了场,而这已经是我能吃到最好的腊肉了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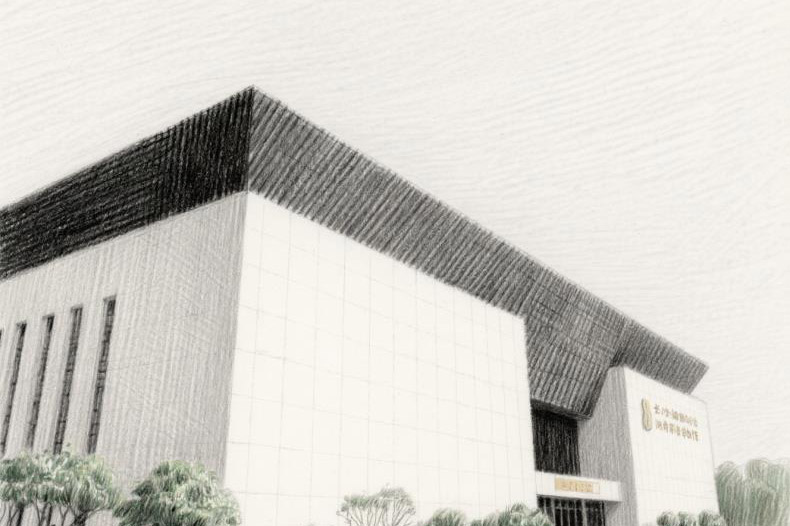
读大学才有机会在外面吃饭,食堂里和校外小店能够吃到的腊肉更为潦草,比起院里阿姨做的都相差甚远。
很长一段时间在我心里,能吃到最好的腊肉都远不如奶奶做的江淮咸肉来得鲜香。
直到那一年,我约摸二十五,因公背着个摄像机到猛洞河拍摄漂流,猛洞河的水真是猛啊,开闸放水,将我们从上游像冲厕所一般被冲下来,一路劈波斩浪,吓得要死都罢了,还要扛着上十斤的设备拍镜头,一路颠簸后惊魂未定到了缓流区,已经累得几近虚脱。
突然见到岸边炊烟袅袅,几个当地人生一堆柴火,支个铁锅在煮东西,烟过船头,一股浓烈熏香扑鼻而来,真正是闻香一刻涎水流,流到肚里饿昏头,昏了头的我们坚决要求艄公靠岸,好歹要讨口饭吃。
万幸,不等我们开口,吃得满嘴油的当地人主动招呼我们吃饭,我们凑将过去,只见熊熊柴火上的那只铁锅里,肥瘦分明的腊肉片在乳白色的汤中翻滚,同煮的还有芽白和青红辣椒,边上高压锅里糙米饭还多着呢。

人在饿极了的时候哪会讲什么鸟甚客气,盛一大碗糙米饭,如三世饿痨一般,夹三五片厚切的肉往饭里一插就迫不及待的往嘴巴里扒。
陈年的脂肪是真的香哩,只用牙齿轻轻一碰那琥珀般的肉,一股暖流喷薄而出,烟熏味牵着着醇厚的小手径直往脑子里钻,微辣鲜香的汤汁渗进饭里,我一口一口往下吞,瞥见同事湿润的眼眶,连笑的时间都没有。
从那天起我才真正明白,每一块腊肉都是有户籍的,这个户籍可以精确到一座山、一条河、一个村、一家人,关乎肉、盐、风、烟火和时间。
腊肉据考春秋战国之前就有,腊字本来念(xī 臘)的音,是腌肉烤干的意思,跟腊月并没有直接关系,有腊肉的时候还没有腊月的概念,如果一定要强行扯点关系的话,那就是腊月期间杀猪过年,天气冷时肉更好晾干吧。
并非只有湖南有腊肉,全国各地都有自己的腊肉,湖北、四川、江西、云南、贵州、甘肃、陕西、河南甚至国外都在做,对,就是那个叫培根的东西。
中国最有名的腊肉是湖南腊肉,这话梁实秋说过,史料记载多个朝代进贡皇帝的腊肉也产自湖南,也许不是每个人都承认,但是反对这句话的人应该不多。

全国腊肉的制作都跑不了腌、晾、熏烤几个环节,各地有各地的腌法,各地也有各地的熏法,说不得哪个地方的味道更好,各有各的风味吧。即便跟腊肉非常接近的火腿和咸肉也是非常美好的,将湖南腊肉比作天下第一,也许大部分原因来自于湖南人对那股烟火的敬意。

在湖南人眼里,没烟子味的肉不叫腊肉,比如广式腊肉,好吃也是好吃的,叫“调味风吹肉”更合理。
在湘西的山村见妇人处理腊肉,将肉从高高的房梁上取下,只见乌漆嘛黑一大条,如一块墨砖,也不晓得多少年的烟火才能将肉熏黑到这般无暇,用清水反复刷洗,将刀在表面来回剐蹭多时方能露出肉之真容。
费力切一大块,到锅里煮上一阵子才算真正清理干净,即便如此,那股柴火烟香依然会从最初加热一直跟到你胃里。
对于湖南人来讲,分辨好腊肉都不用吃进嘴巴,夹一片蒸好的肥肉对着光一看,色如琥珀,鲜亮透明的绝不会差,这种状态是烟火和时间给予的,急不来,更怠慢不得。

好腊肉随便做都好吃,薄薄的切了炒大蒜、炒黎蒿、炒藠子和一切与“五荤”相关的植物都是绝配;切厚些或蒸或煮无需调味皆是馥郁芬芳;切碎与米饭糯米同蒸煮,待到油脂浸润,其它旁的菜都多余。

近些年一些大馆子求来好腊肉,视若珍宝的切那么几片,整整齐齐码好,只敢蒸熟,摆到桌上流光溢彩香气扑鼻,往往吃得客人摇头晃脑,只十数片便可镇席。
湖南人如此迷恋烟火,以至于尝试着熏制一切,鸡鸭鱼肉,猪狗牛羊,田鸡鳝鱼,王八兔子……甚至茶叶都要熏它一熏。
也许迷恋的不单单是味道本身吧,也许这种味道产生的过程甚至更加迷人,那种漫长的等待与守候以及时间与烟火的考验,虽然最终面目全非却成就了厚重深沉,这又何尝不是一种修行呢?
免责声明: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,与本站无关。其原创性、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,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、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,请读者仅作参考,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。
举报邮箱:3220065589@qq.com,如涉及版权问题,请联系。

















网友评论